译文 | 透视科技界对永生的执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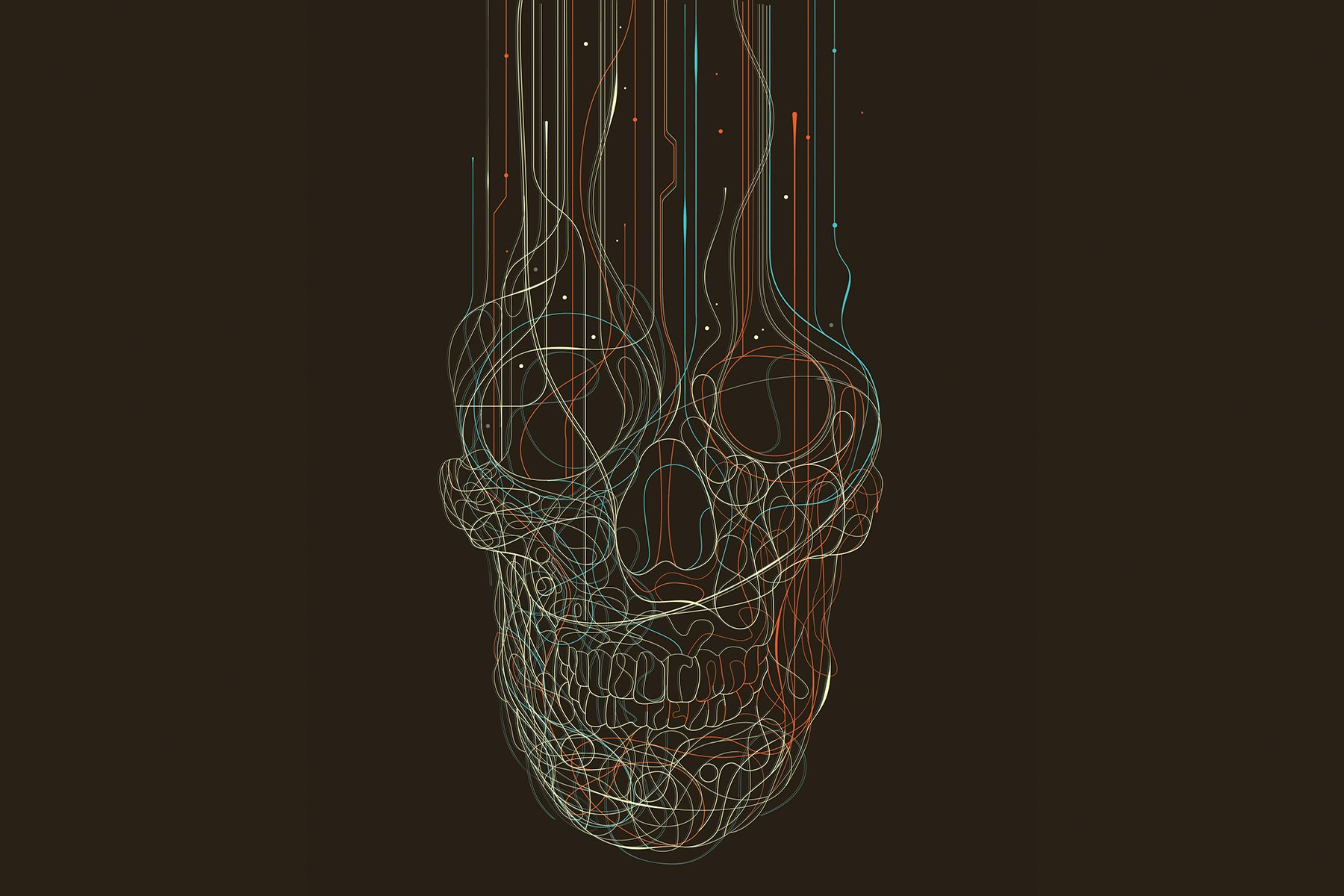
图:Harry Campbell
**译者按:**健康与科技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用编程思维研发的代餐,到指导生活饮食方式的 DNA 检测,再到保存人体的冷冻库——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产品令人眼花缭乱,其形式越发新奇、承诺越发大胆。这在给我们带来对未来美好预期的同时,也不禁令人心生疑虑:科技改造人类的边界在哪里?这种追求会不会走向理性、科学和道德的反面?本文中,作者以对《成为机器》(To Be a Machine)一书的评述为载体,追溯了这股硅谷风潮的文化根源,探访了一些「科技延长生命」理念的忠实信众,剖析了其重视未来却忽视当下的内在矛盾,最终指出发展技术不应走向极端,科技和人性不应相互对立。无论作者的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在滚滚前进的技术浪潮中,放慢步伐做一些思考总会是有益的。
1994 年十月,《连线》杂志刊载了一篇加州亚文化专题报道,并起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标题:《遇见负熵主义者》(MEET THE EXTROPIANS)。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负熵主义(Extropianism)是一门关于超越的哲学。只要有了技术和正确的态度——激进的个体主义、冷静的理性主义、和其他一些模糊的自由主义倾向——这场运动的信众就能「超越人类」。他们将会成为「超人类」(transhuman),拥有「急剧增长的智力、记忆力和体能」,甚至或许能成为后人类(post human)。他们想象出这样一种未来:人脑将会被下载、保存,以遗后世;而人体,也将通过冷冻术的方式被保存下来。
这些怀着超自然理想的专业人士用「负熵」(extropy)一词来表示「熵」(entropy)的对立面。所谓「熵」,就是一切事物走向最终消亡的过程,他们设想出一种生活方式来与之对抗。负熵主义者发明了一种浮夸的握手方式来相互问候,并自称为 VEP,也就是「超级负熵人(Very Extropian Person)」。《负熵》杂志(Extropy)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他们对「存在」的看法。「你喜欢什么样,就可以是什么样,」《负熵》设想道,「你可以变大、可以变小;可以轻比空气、展翅飞翔;可以瞬间移动、走壁攀墙。」2006 年成立的负熵学会(Extropy Institute)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持续进步的象征」。
早期的负熵主义看起来并无新意,无非是一群反文化主义科技爱好者的集会。但他们却催生了科技行业一个领域的舞台,这个领域近来获得了来自慈善、风投等领域的巨额投资。长生不老、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和其他后人类式的目标仍然是科技乌托邦讨论的重大事项,但它们从未如此成为显学。风投资本家 Peter Thiel 正试图探索用输血来延缓衰老的方法。(「Peter Thiel 非常、非常热衷于年轻血液,」《Inc.》杂志去年夏天在报道中写道。)谷歌创始人之一 Larry Page 给一家叫做 Calico 的实验室投了 7.5 亿美元去研究抗衰老技术。2012 年,谷歌任命 Ray Kurzweil 为工程主管,他也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笃信人工智能很快就会让人类超越生物学理论的限制。
比起负熵主义者的理想,这些新目标更容易让人们正眼相待,但要弄清它们会将我们带向何方却没那么容易。在《成为机器》(To Be a Machine)一书中,都柏林作家 Mark O’Connell 试图渗入这群超人类主义者,探寻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O’Connell 是《Slate》杂志的书评作者、之前也做过学者。比起评价技术本身的价值,他对发明技术的人和技术背后潜在的哲学问题更感兴趣。在深入观察追求永生的过程中,他关注那些试图避免或是大大推迟死亡的人——科技空想家、亿万富翁、未来主义者。「我想知道,」他写道,「是怎样一种对技术的信念,才能让你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
这或许是在委婉地说,长生不老理念的影响力是与其实际可行性挂钩的。[既然]长生不老是镜花水月,那它如今怎么就成了一个大生意呢?
未来这个概念从来就是财富之源;越是把它说得抽象模糊,就越是有利可图。尽管 O’Connell 没有把视线完全集中在硅谷(因为超人类主义者遍布世界各地),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毫无疑问是一个加州式的工程。自我提升课程、健身狂热、节食风潮、对中产趣味独特品牌的拥趸,是加州长久以来的传统。加州人是自由的推动者,活出范儿是他们至高无上的追求。
如今,这种乌托邦式的未来主义可以披上新时代管理哲学、公司健身、智慧 2.0 (Wisdom 2.0)年会的外衣,将科技界的杰出人物和精神领袖汇聚一堂,从 Eileen Fisher、Alanis Morissette 到 Slack 和 Zappos 的 CEO。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风投支撑的产品,不仅承诺能让你变得更健康、更有效率,更能从根本上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从 Soylent(一种代餐饮料)到 nootropics(一种据称能提高人认知能力的胶囊),投资人追求的是延长青春、增强神经、强健体魄。
当然,与其给人的感觉相比,这些产品本身大多并没有那么新奇。硅谷没有新点子,只有新花样。Soylent 看起来很像 SlimFast,一种 20 世纪 70 年代就针对节食女性推出的蛋白质饮料;nootropics 中往往会含有 L-茶氨酸(提取自绿茶)和咖啡因。这些公司之所以能给人耳目一新的错觉,其网页设计功不可没——精致的门面设计是可信度的标志,也暗示着幕后会有惊人的黑科技。推广这些产品靠的是吸引工程师中的工作狂人,他们给自己找了些高科技难题,然后拿这些高科技解决方案来以毒攻毒。但这些产品的预期并不局限于(服务)硅谷,只是带着一股提升自我、科技改善生活的独特加州味。
很难不把超人类主义也看作无非另一种新瓶装旧酒。O’Connell 书中的许多话题就建立在这种假定上。Aubrey de Grey,一位生物医药方面的老年学家,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Anders Sandberg,一位神经学家,致力于「上传」思维,希望能成为一台真正的「情感机器」。他还是一位艺术家,创作了类似于互联网早期科幻迷艺术的数字场景,并起了一些诸如「复制者之舞」「空中城堡」之类梦幻的名字。Zoltan Istvan 曾经是一名记者,自称发明了「岩浆冲浪」(volcano-boarding)运动,还参与了总统竞选,其间他乘坐一辆棺材形状的巴士环游全国,以提高超人类主义的认知度。他还宣扬一套支持科技行业的政纲,呼吁保障统一性的基本收入;鼓吹一份《超人类主义权利法案》,以确保「人类、有知觉的人工智能体、电子人及其他高级智慧生命形态」被「赋予统一的、免于非自愿痛苦的权利」云云。

Aubrey de Grey 的非营利机构关注无限延长生命。摄影:Peter Searle/Camera Press/Redux
还有一位叫做 Max More 的负熵主义创始人,在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运营着一家 Alcor 生命延续基金。Alcor 是一个人体冷冻保存机构,它储存尸体——更准确地说是分离下来的头颅,好在未来的某一天将其拼接到人造躯干上,其服务对象是那些希望能在技术允许时马上复活的人。O’Connell 写道,这些尸体,「被认为是处在停滞状态、而非死亡,它们留驻在现世和一个与之或即或离的世界间的过渡地带,静止着。」Alcor 是全世界四个人体冷冻保存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居住着 149 位「患者」,70% 是男性。(Alcor 同时也冷冻保存宠物。)最小的患者是一个两岁的孩子,死于一种罕见的小儿脑癌;发布于 Alcor 网站上的「病情概述」表明她的父母(均在世)也希望接受冷冻保存。「毫无疑问,身边有挚爱亲人的面庞作伴,将使她的重生更加轻松愉快,」病情概述如此结尾道,让人既感到希望、又感到心碎。但迄今为止,科学还未表明这种起死回生将成为现实。这个在不确定的未来把人的思维「上传」到一个有生命的新躯体的梦想,仍然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
致力于实现永生的人思考的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希望把人类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另一派希望使肉体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健康。Randal Koene 和 Max More 一样属于前一派。他研究的不是人体冷冻,而是「思维上传」,即构建一种可以独立于肉体存在的思维。他创办的非营利组织 Carboncopies 的目标,是「通过数字化自我复制达到实质上的永生」。Konoe 将思维上传比做划独木舟。「这就好像一个精通划独木舟的人,他觉得独木舟就是他下肢的延伸,坐在独木舟上的感觉完全是自然的,」他对 O’Connell 说。「因此,把思维系统上传或许并不会那么让人感到震惊,因为我们已经身处这种将物质世界当作肢体的关系之中,世上有如此多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是自己身体的延伸。」
Aubrey de Grey 则属于主张维持肉体的第二阵营,他的目标看起来略显温和:只求延长生命,不求避免死亡。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主要关注对心脏病和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也研究其他常见病。(与其他很多有关超人类主义的机构一样,SENS 也收到了 Peter Thiel 的投资。)De Grey 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推广了「长寿逃逸速度」(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O’Connell 这样解释这个概念:「时间每推移一年,长寿研究取得的进展就使得人类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超过一年;理论上,这种趋势将让我们最终超越死亡。」这种超人类主义的观点很容易被斥为过于极端:人类人口如此之多,如此断言过于自大。然而,在这个慨叹人性泯失的时代,在这个对未来趋势愤世嫉俗的时代,超人类主义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你可以说它是奇思妙想,也可以说它是过度乐观。
追求不死或许是夸下海口却不兑现的极端例子,但还是做出了一些成果。的确,负熵主义抗衰老的梦想有许多已经变成现实,尽管这些成就在今天看起来并没有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新潮。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发展使我们的长寿超越了前人的想象。我们和手机共枕而眠。假肢越来越量身定制,也越来越让人负担得起。机器人实施的显微外科手术模糊了人类技能和机器技能的界限。在更古板的人(也是最有钱的人)看来,对超人类主义的追求无非是生物科技而已。
O’Connell 的关注重点在于执着于永生的超人类主义极端份子,但他也访谈了一些主张用渐进方法让人类一步步接近长寿健康的人。Miguel Nicolelis 是一位研究人脑–机器连接技术的神经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可以用脑电波控制的机器人盔甲,并在 2014 年世界杯上进行了展示,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和机器人在未来可以怎样协作。这项成果一个显而易见的应用就是帮助截瘫患者提高活动能力。科技并不需要我们颠覆对现实的认识,从小处改进同样是可以的。
Nicolelis 似乎并不像其他技术专家那样热衷于规模化。尽管证明了脑部活动可以翻译为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被翻译为[机器的]动作,他对全脑模拟这样的大规模计划也并不感冒。「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大脑状态的本质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他去年告诉《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说。「人类喜欢用类比、隐喻,喜欢作出预期和预判,这些是算法不能体现的。」
随着超人类主义逐渐改变人类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它也将改变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到 100 岁而无疾病,那么社会、经济和环境都将发生剧烈变革。童年应该是多长?如果「婴儿潮」那一代人还能投 50 年票,政治图景会变成什么样?O’Connell 对超人类主义的探寻,恰逢我们的民主制度空前脆弱之时。财富愈发集中于一小群人手中;尽管未来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但对如今许多人来说,未来似乎格外暗淡。想象一个超人类主义宏愿全部成真的未来是令人兴奋的思维实验,但这兴奋很快就会退潮,变成反乌托邦式的想象:地太少、人太多,而且,如果人脑都是从一个世纪前上传来的,它们都会变得像废旧软件一样。
无论超人类主义者的目标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雄心勃勃、多么天马行空、多么切实可行,它们都忽略了全面设想目标实现后社会将是什么样。重视速度和规模的硅谷中人先进行创新,成功后再匆忙解决不良后果,这绝不会是第一次。
超人类主义有一个关键承诺、但同时也是其根本问题所在:它让信奉者免于承担对当下的义务。正如比尔·盖茨在一次 Reddit 上的「随意提问」活动中所说,「在人类还没有摆脱疟疾和肺结核的时候,有钱人却在为活得更长而投资,这似乎太自私了。」O’Connell 也觉得,「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对研发 AI 更感兴趣,却不关注消除「自己国家荒谬的收入不平等」,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诚然,试验是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研究者也宣称自己的工作在未来将造福全人类。但问题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又会属于谁?
超人类主义中也有一些让人深感悲伤的元素。这种超越人类的渴望让人回想起那些提升自我的教义,它滥觞于上世纪中期的美好时代,对加州产生了深刻影响。可是,对更好世界和更好自我的预期却难以摆脱当下的现实。在总统选举和就任间的数周里,腐败的猖獗、对宪法中自由权利的扭曲,还有其他很多糟糕的事情,进入了我们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幻想改造人类、实现永生的未来似乎是自我放纵;哪怕只是幻想一下未来,似乎也是自我放纵了。
然而我并不能因为超人类主义者渴求更多而责备他们,渴求从生命中得到更多也好,渴求生命本身更长也罢。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这本 1999 年出版、如今已是超人类主义著作标杆的书中,文学批评家 N. Katherine Hayles 详细阐述了她理想中的后人类世界:
如果将一个把肉体当作时髦配饰、而不是生存根基的后人类文化比做我的噩梦,那我的美梦应该是这样的:后人类拥抱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却又不被无限力量和灵肉分离以求不死这样的幻想所引诱……他们明白人的生命植根于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而我们的长久存续皆有赖于此。
在我看来,[O’Connell] 关注后人类目标中的极端例子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一直在从各个方向缓慢推动着生命的边界。Hayles 的想象显然处于一个中庸的方向:人会死、也会犯错误。但在她的描绘中,这种发展方向并不过时,相反更加可控——也更有人情味。
(本文最初于 2017 年 2 月 26 日发表在 New Republic 网站上,作者 Anna Wiener 是一名旧金山作家,时常为 New Republic 供稿。)